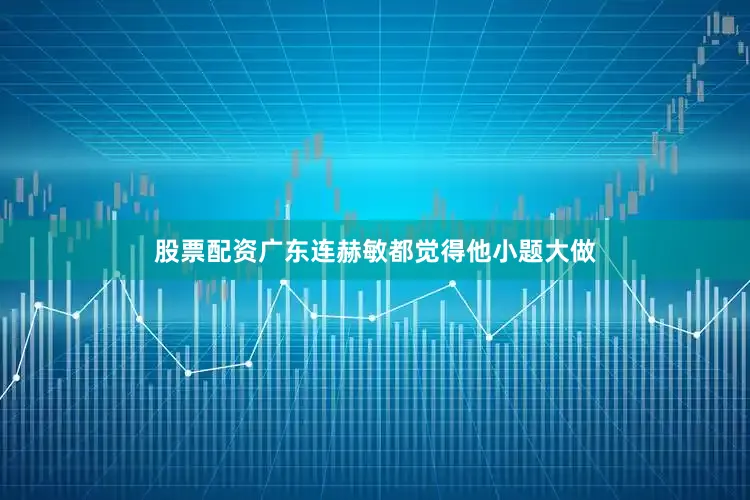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喜欢旅行,另一种人不喜欢旅行。不喜欢旅行的人,各有各的原因,而喜欢的通常没有原因,就是喜欢。当然,也可以有第三种人,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旅行。还有些人,只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旅行。说白了,他们假装旅行,就像他们假装看展、喝茶、读书、听音乐一样,只是为了发照片、发视频。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属于那种天生喜欢旅行的人,“跨越国境”是他血液里的基本冲动。一定是听到了他衷心的呼告,命运安排他做了驻外记者,让他如鱼得水。他的行囊里一直带着一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是《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这个书名的由来。
认真说来,这个书名有一点误导,因为其中的“旅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希罗多德和卡普斯钦斯基都是去工作的,只不过看起来像在旅行,这倒也跟那些假装旅行的人一样。在接近全书结尾,卡普希钦斯基说:“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语‘历史’一词的意思更多是‘调查’或‘探究’,这两个词无论用哪个,都更符合作者的意图和抱负。”书名中的“旅行”一词也应作如是解。或者,借用时兴的说法,这个书名约等于“与希罗多德一起游学”。
做“游学”生意的广告都会引用一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对等、互补,通常更偏向于强调后者。而卡普钦斯基发现,“通过阅读更多书记、研究地图、观看绘画和照片,能进一步延长这些旅程,加深记忆与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比真实的旅行更有优势——如此卧游的人可以随时停下来,平静地观察,回放之前的画面,如此等等”。正如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实在没有资格说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一个不读书的人,简直也没必要旅行。本来,想要增长见识,读书乃是最便捷的方式,不读书而旅行,岂不是舍近求远?至少,对于读书人而言,旅行终究是可有可无的。最极端的例子是康德,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哥尼斯堡,可是有人胆敢宣称自己对于世界和人性的认识比他更全面、更深入吗?
展开剩余75%在1950年代中期的波兰,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开始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第一次与他者的相遇”是受派遣去印度,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对于突然到来的“第一次”,他毫无准备,几乎一无所获。不过,他也“因此发现了新世界”,并且懂得了“这个世界教人谦逊”。说真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就算得上一个很大的收获。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那是一个正确的起点。
接着,1957年,他到了中国,“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提着装满书的袋子”。尽管他做了一些准备,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还是陷入了困境。艰难的中文当然是障碍之一。另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不妨说是文化吧。无怪乎他借长城发出这样的感慨:“它是世界奇迹之一。但长城也指向了人性的弱点。长久以来,地球上的居民似乎没能真正地进行沟通和协商,并共同决定如何最有效地运用巨大的人类能量和智慧。”——这个判断或许有待商榷,这里暂且放下不谈。我很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在三四十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当时,他“离开中国的心情,就像离开印度一样,带着失落,甚至悲伤”,但是紧接着又让人眼睛一亮:“与此同时,这次离开也带有某种决心。一个全新的世界……完全吸引了我,让我沉溺,难以自拔。我被一种深刻的迷恋攫取,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渴望,那种让我自己完全沉浸其中,被它融化,与这个陌生的宇宙融为一体的渴望。”——不过,他并不想成为“汉学家”,虽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同样吸引着他的是“尚未遇见的人、尚未走过的路、尚未见过的天空”。
到了这里,经过长达80页(占全书四分之一)的铺垫,卡普希钦斯基正式引出希罗多德。并且,他立即指出了《历史》这本书的关键,在于希罗多德的写作宗旨是“防止人类功业的痕迹被时间抹除,保留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取得的卓绝成就,特别是记下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互相争斗的原因”。而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如此描述希罗多德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地中海-近东地区:“这是个阳光明媚的世界,有海洋和湖泊、高山和绿谷、橄榄和葡萄、羔羊和麦田——一个每隔几年就会血流成河的明亮的世外桃源。”
在每一段文字中,你都可以感受到,卡普希钦斯基与希罗多德隔着两千多年时间,发生着强烈的共鸣,而且正巧两个人在地表上的活动轨迹似乎有很多是重合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又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在说另一个人的时候,就像在说他自己,只要把那些不可改变的外在差异忽略不计。
卡普希钦斯基毫无保留地赞誉希罗多德:“希罗多德以孩子般的痴迷的热情去了解他的世界。”“他是第一个发现世界文化多元本质的人。他第一个提出,需要接受和理解每种文化,而要理解它,就先得认识它。”如此这般的赞誉(称为“第一个”)在学术上是不是足够严谨并不重要。至少,卡普希钦斯基让我们确信,希罗多德是一个混血儿,“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他试图了解、理解和描述差异”,而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有很多个世界。每一个都不同。”
作为一个希腊人,希罗多德原本可以享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我们知道,“野蛮人”(barbarian)一词,其古希腊语词源的本义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类似于曾几何时的某些巴黎人、某些上海人对本地之外的各种人的态度。希罗多德“批评他的同胞们的骄傲”,他改换了称呼,把波斯人、埃及人、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乃至印度人等等统称为“非希腊人”,这就变成了一个中性的称谓。实际上,他还可以更进一步。深究起来,古代世界的诸神和英雄的身世及其纷纭复杂的传说,从一个侧面表明,古希腊文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换言之,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化之中,包含着诸多“非希腊人”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希腊人,非希腊人,本是一家人。日本人稻盛和夫说:“人,不走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对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其中之一就是让人不要封闭起来,夜郎自大。
如前所述,希罗多德行万里路,写作《历史》的目的,一方面是记录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卓绝成就,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特别是记下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互相争斗的原因”。大约在他出生那一年前后死去的赫拉克利特,有一个残篇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也就是把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争斗,视为宇宙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论断得到后世诸多伟大思想家的认同。迄今为止,战争依然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特别令人激昂、值得不断续写的光辉篇章。然而,尽管希罗多德没有这么说,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人与人为什么要互相争斗?——这个“希罗多德之问”注定得不到回答。他只能在他的字里行间默默提示后人: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争先恐后,保持节制,保持谦逊……
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卡普希钦斯基引述了大量《历史》中的内容。我们看到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起因、过程、结果。透过战争的残酷(有些更为残酷的事件发生在战争之前和之后),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幽暗。然而我们又不期而然地遭遇了“卡普希钦斯基之问”:如果理性统治世界,历史还会存在吗?——卡普希钦斯基还真是个爱提问题的人,而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最扎心的问题,它似乎也可以用来质疑柏拉图式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及其各种翻版的可能性。
带着同样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卡普希钦斯基说希罗多德:“他没有愤怒,没有敌意。他试图了解一切,搞清楚为什么有人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行事。他从不抱怨人,只责问制度;个体并非生而邪恶……使他邪恶的,是他恰好生活在其中的社会配置。”从人性或者制度入手,这两种不同的起点和取向见仁见智。而希罗多德和卡普希钦斯基“从不抱怨人,只责问制度”,既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也是对人的怜悯和仁慈;他们明明看到了历史的轨迹并不遵循理性,却又始终对人有信心。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直有兴趣去探究不同的人,探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同类可能有的、应该有的样子。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踏上行旅。
作者:朱生坚
编辑:杨延超
发布于:上海市盛达优配-股市杠杆公司-股票在线配资-配资炒股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杠杆网站排名这不就是“细节见人品”的活生生写照吗?可能有人会说
- 下一篇:没有了